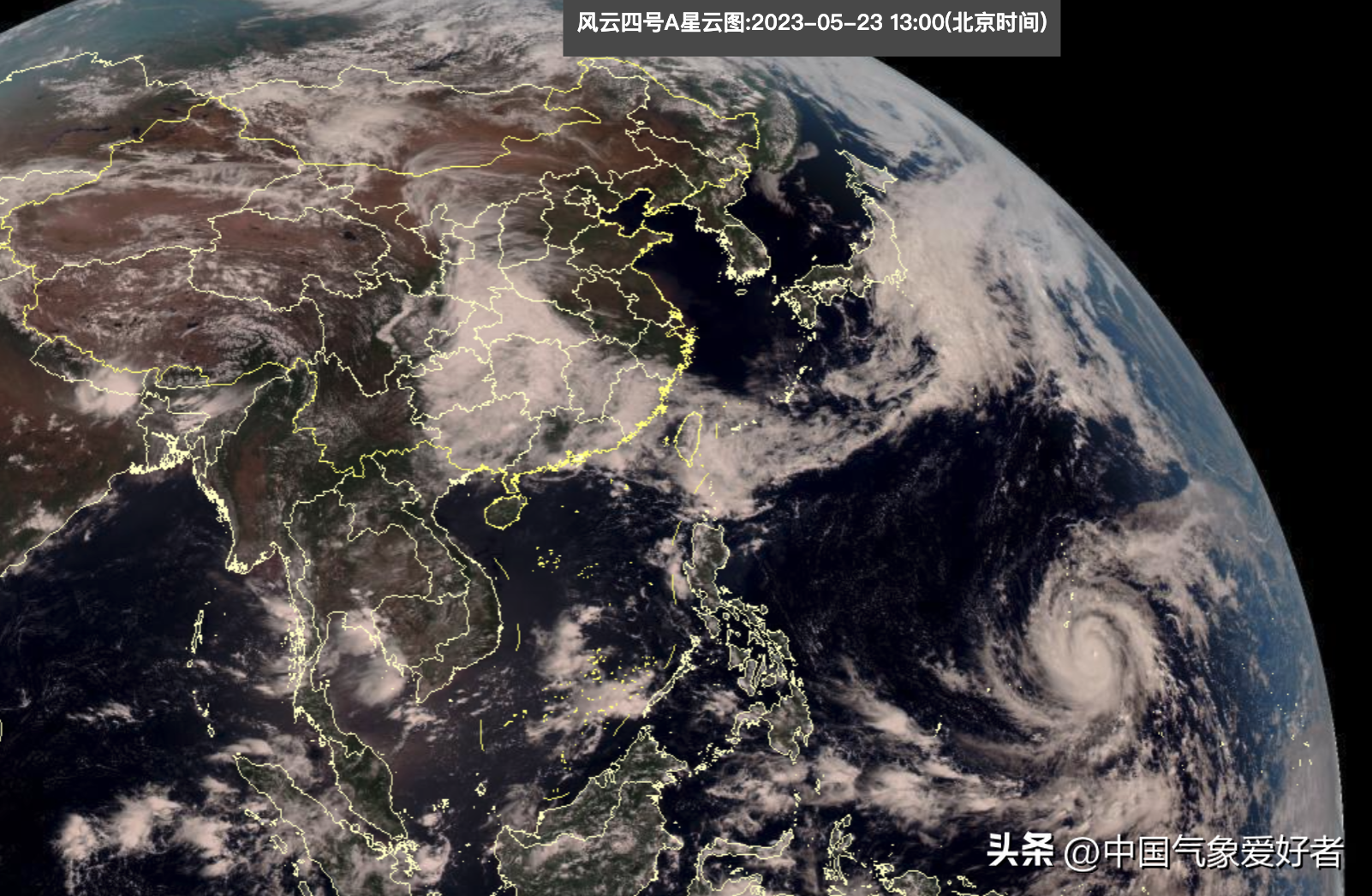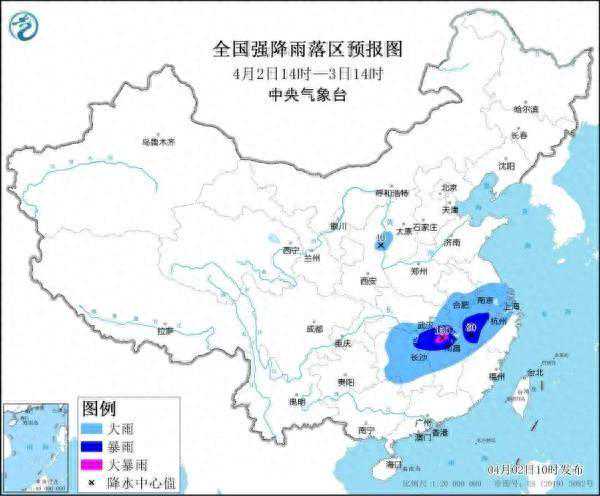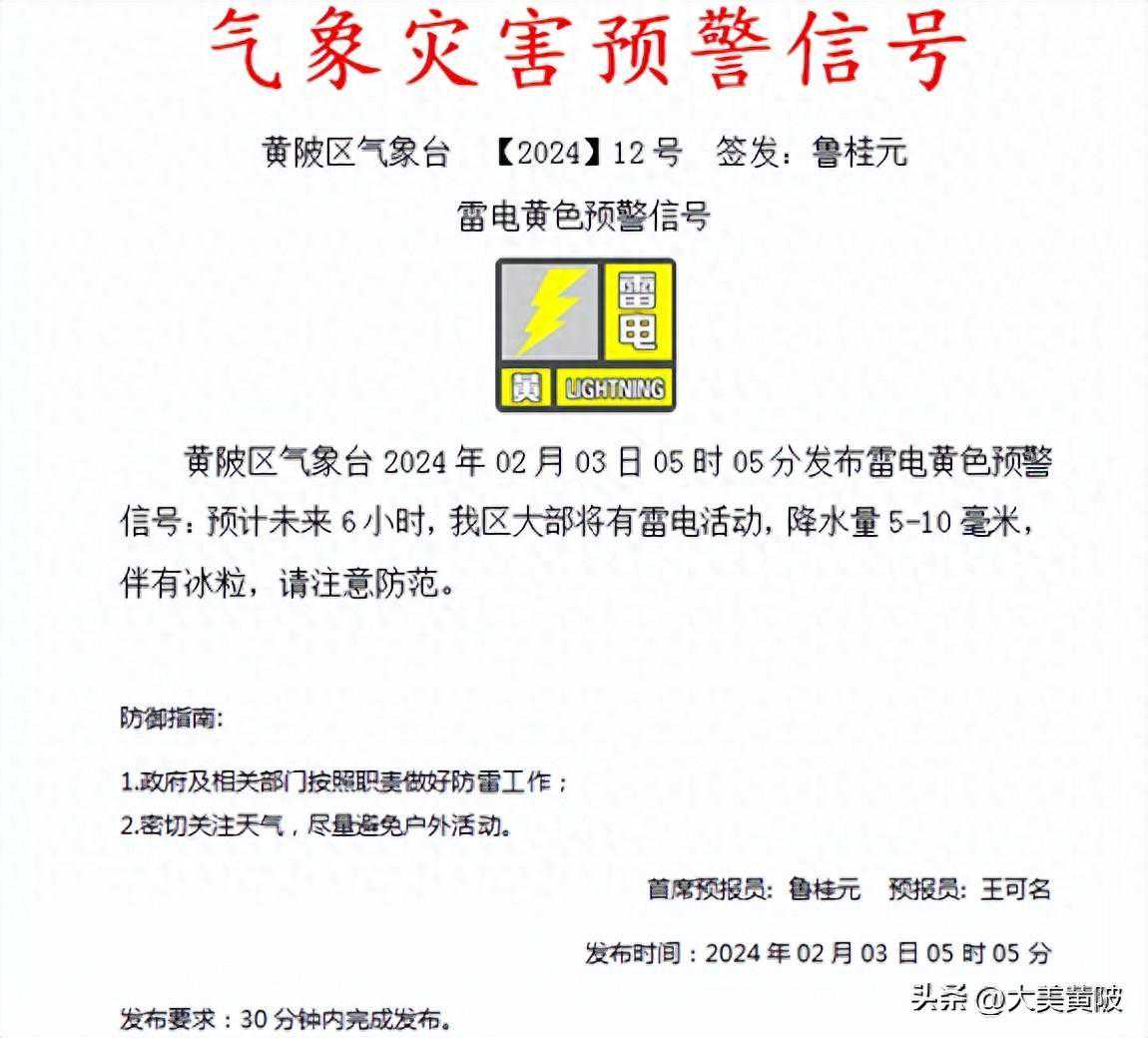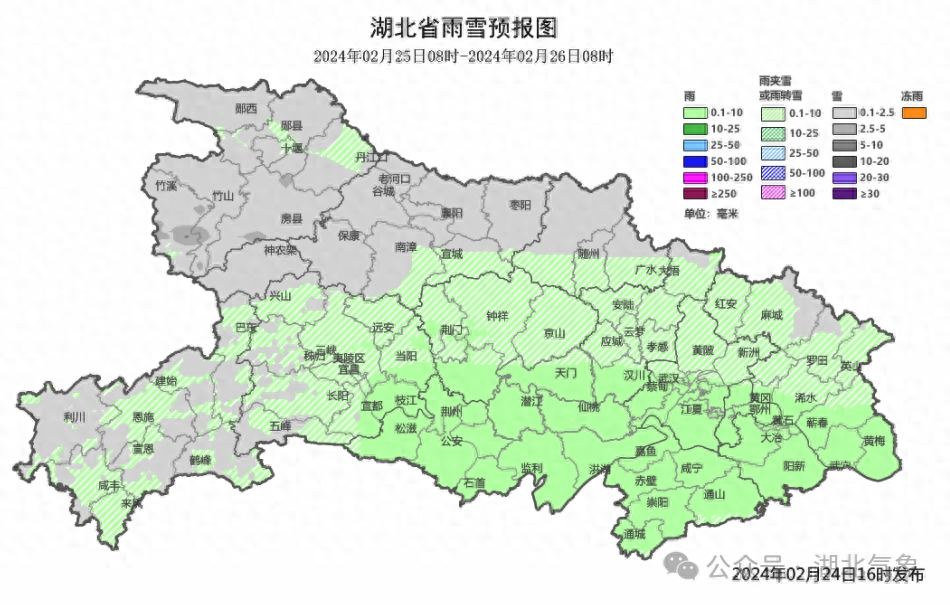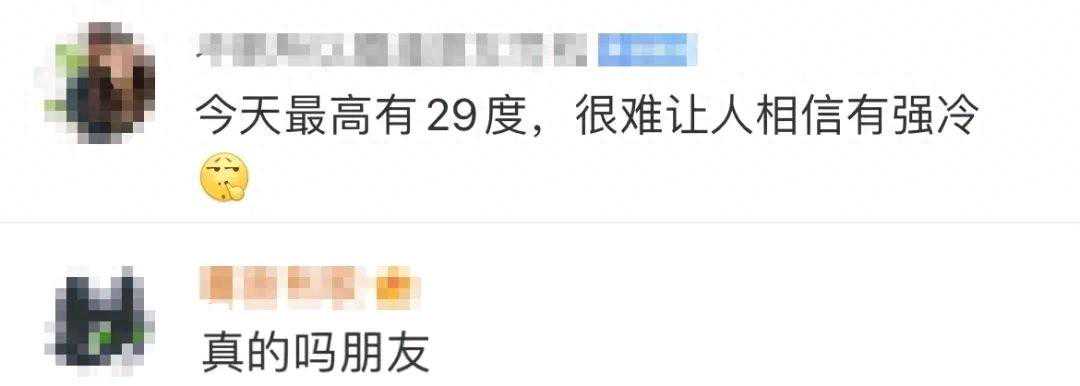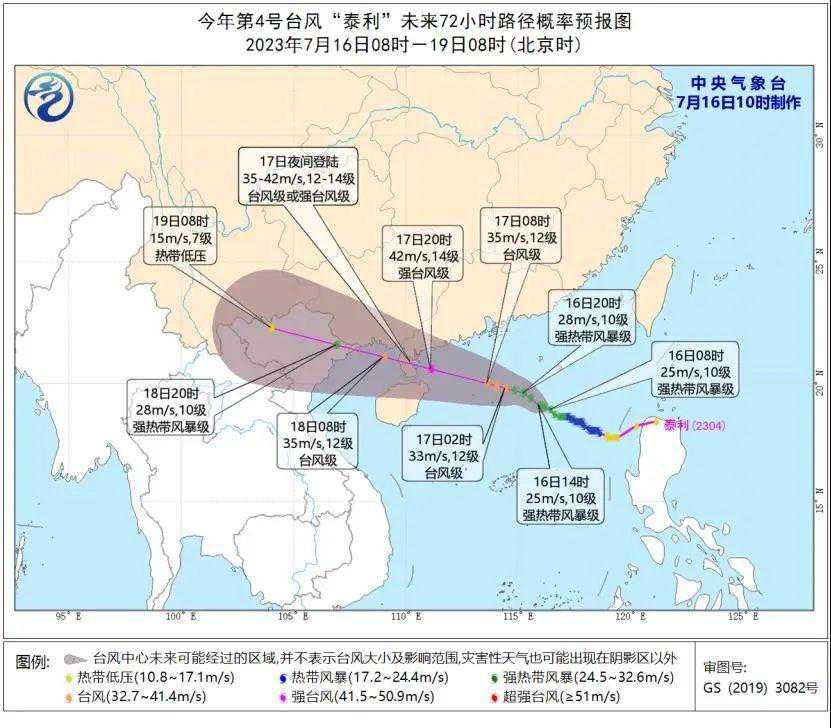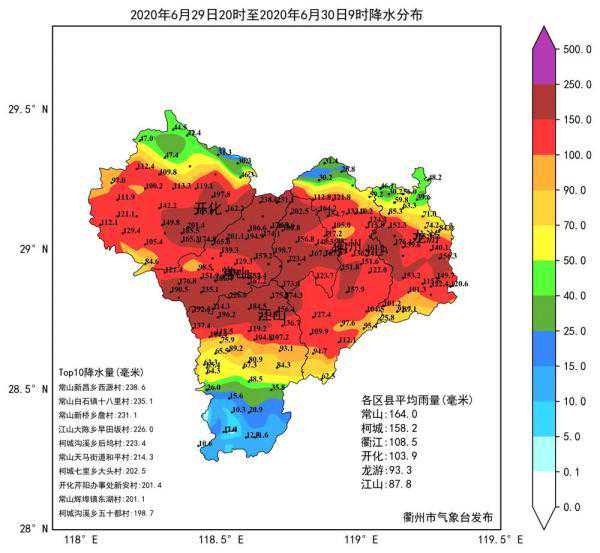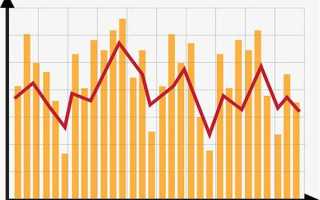庄子的时代有助于勘破人世的真相:世界变动莫测,人的吉凶祸福以至生死都只是随世浮沉而已。《人间世》里充满了进退不得、动辄得咎的险难,《德充符》里触目皆是遭受刖足之刑的人,哪怕与“孔子”齐名的贤者王骀也不能幸免。险恶的情势,逼迫敏锐好思之人从日常的疲态中振作,思考存在的意义。对于人类文明史、思想史的演进而言,大哲学家、大宗教家多出于忧患穷极之境、无奈呼天之际,也是被反复验证的道理。庄子的思想中特别显著的就是其深沉而积极的命运感。
命运感的最高体现是人对待死亡的态度。先秦的儒家哲学秉承孔子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的态度,对死亡的话题保持这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。在道家哲学里,庄子有大量关于死亡的思考。他提出了“善夭善老,善始善终”(《大宗师》)的主张。
庄子用知识的不可靠性来质疑好生恶死的人间“常识”。《齐物论》里有一个故事:丽戎国有个美女,是一位戍边人的女儿。当得知要嫁到晋国国君时,她哭得泪水湿透了衣襟。后来,当她在王宫里安享尊荣的时候,才觉得当初的哭泣实在愚蠢。庄子借此发问:谁知道死后的人不会像丽姬悔泣一样,自笑当初怕死的无谓呢?
庄子还以中国人熟知的阴阳宇宙观来解释生死现象。他把生死联系于自然的昼夜交替:“死生,命也;其有夜旦之常,天也;人之有所不得与,皆物之情也。”(《大宗师》)他又把生死联系于一昼夜里的劳作和休息:“大块载我以形,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,乃所以善吾死也。”(《大宗师》)死亡,是整个生命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,正如黑夜是一天光阴的一部分,就像睡眠是一天生活的一部分。作为宋代道学生死观的源头,张载提出了“生,吾顺事;没,吾宁也”(《西铭》),跟庄子的气化观也有渊源关系。
不过,庄子对于疾病与死亡,除了这种斯多亚式的理性观照之外,还特有一种诗意的态度。
庄子把死亡看作是一场壮丽的谢幕。庄子的妻子死了,他敲打着盆子为“偃然寝于巨室”的伴侣唱歌(《至乐》)。待到他自己要死了,也谢绝厚葬。他说:“吾以天地为棺椁,以日月为连璧,星辰为珠玑,万物为赍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?何以加此!”(《列御寇》)死亡,使人终于能够卸去礼貌文饰的束缚,回归那装点着星辰日月的广大富庶的家园。这不仅是一般的理性的“达观”,还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审美境界。
《大宗师》里也有一个故事: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,四人相与语曰:“孰能以无为首,以生为脊,以死为尻,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,吾与之友矣。”四人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,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,子祀往问之。曰:“伟哉!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曲偻发背,上有五管,颐隐于齐,肩高于项,句赘指天,阴阳之气有畛。”其心闲而无事,蹁跹而鉴于井,曰:“嗟乎,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”子祀曰:“汝恶之乎?”曰:“亡,予何恶!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,予因以求时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,予因以求枭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,以神为马,予因以乘之,岂更驾哉!且夫得者,时也;失者,顺也。安时而处顺,哀乐不能入也,此古之所谓悬解也。而不能自解者,物有结之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,吾又何恶焉?”(《大宗师》)
子舆和他的朋友们由“知生死存亡之一体”而互为知音,“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”,不仅由于这种沟通经验超越了一切外在的言辞和交际手段,也由于他们在宗教感的层面上领会了默契:在对于生死的觉解上,也在对于存在体验的分享当中,人超越了个体的有限性。就外在的躯壳来看,子舆弯腰驼背、五官上翻、腮帮子贴在肚脐上、双肩高过了头顶,身体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严重变形了,这是阴阳之气严重不和的结果。但子舆的“闲心”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他还蹒跚着挪到井边,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。他不以为这种扭曲的形体是丑恶的,因为这是天地造化的宏伟进程的一部分。他兴致勃勃地设想如何让接下来的过程变得更为有趣:如果自己死后,左臂化成了鸡而右臂化成弹弓,不妨打来吃烤肉;如果臀部化成了轮子,那就可以以神志为马,驾车遨游也不错。子舆像一出戏的导演一样期待着创作的惊喜,像一个不知生死为何物的顽童一样,等待着盼望中的游戏,全然没有病中人所面对的死亡的那种忧苦的、幽暗的,甚至是恐怖的色彩。这是一个形残德全的人独有的意象世界。他在这个奇伟的意象世界当中心闲以观,欣然待化,平静地走完了也许困苦却无忧无惧以至意趣盎然的人生。
庄子把“丧己于物”的不自由状态称为“倒置”(《缮性》)或“心死”(《田子方》)。人被各种“物”所缠绕,所以不能够从倒置的状态里自我解救。子舆心闲无事,是因为安时处顺、哀乐不入的心胸解开了捆缚生命的绳索。这就是庄子多次提到的“悬解”。由此,我们不同意一种关于庄子的流行的看法,即认为他是一个消极的、逃世的,甚至是滑头的相对主义者。庄子对于躯体、祸福、名利常常抱有无所谓的态度,但对于自由、意义的彰显、价值的实现却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。庄子是一个尝过了世间百味之后仍然没有心死的人。
命定不可改变的祸福寿夭恰恰能彰显出人心的自由和尊贵。“受命于地,唯松柏独也在,冬夏青青。受命于天,唯舜独也正,幸能正生,以正众生。”(《德充符》)庄子以松柏比德,重在其无惧于外在环境的戕害,凸显其独立不屈的尊严。大凡具备宗教感的思想家,都有独面生死、独行其道的勇气。孔子曰“莫我知”,孟子曰“独行其道”,老子曰“我独若匮”,庄子说:“出入六合,游乎九州,独往独来,是谓独有。独有之人,是谓至贵。”(《在宥》)自由的心面对着群物的羁绊,犹如雄入九军的勇士,有着万夫不当的气概。圣人以此心“正生”,也就是彰显自己生命的意义。圣人还以此心“正众生”,是为天下后世知心之人开显生命的意义。
庄子的“独”还特有一层怅惘的诗意。《山木》篇里,有人给鲁侯讲述了一个“其生可乐,其死可葬”的理想国度,有如下的对话:
君曰:“彼其道远而险,又有江山,我无舟车,奈何?”市南子曰:“君无形倨,无留居,以为君车。”君曰:“彼其道幽远而无人,吾谁与为邻?吾无粮,我无食,安得而至焉?”市南子曰:“少君之费,寡君之欲,虽无粮而乃足。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,望之而不见其崖,愈往而不知其所穷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,君自此远矣!故有人者累,见有于人者忧。故尧非有人,非见有于人也。吾愿去君之累,除君之忧,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。”
理想的世界,道阻且长,总是由于人背负的担子太重,牵制的仆妾太多,而人犹惴惴以为不足。现实的此岸与理想的彼岸由此江海横绝,越来越远。市南子说,减少对于外物和他人的依赖,才是自我解缚道路上的舟车与粮食。浮于江海,缘在身轻,放下了对物的依赖,心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从前,你由于软弱而躲藏在众人之中,此刻,送行的人已离你而去。牵挂和被牵挂,操心和担忧,至此都应决然抛弃,人终归要独自承担存在的意义。

选自叶朗主编《中国美学通史》


![高平市气象台发布沙尘蓝色预警[Ⅳ级/一般]](/imgs/baidou-v2/upload/default/CE71616BF.jpg)